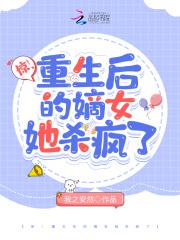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后记(第2页)
后记
banner"
>
前一时有人提到我出版于1990年代初的《北京:城与人》与《地之子》,认为后者似乎较前者厚重;但由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,前者受欢迎的程度远在后者之上,不知何故。
我回答说,两本书的写作,投入确有不同。
写《北京:城与人》,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“京味小说”
。
在我的学术作品中,这本书写得最轻松,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。
它的“受欢迎”
,多少由于机缘——出版时恰逢“北京文化热”
。
后来“北京”
、“城市”
热度不减;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。
还说《城与人》之后,我至今保持了对“城市”
的兴趣,旅行中往往持“考察”
态度,对近几十年的“城市改造”
怀了忧虑。
收入本书所在“系列”
中的《世事苍茫》一辑,其中的《城市随想》与纪游诸作,就可以读作“城市忧思录”
的吧。
在我的学术作品中,《城与人》是被认为好读的一本。
我曾经说起过,学术写作中,我会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对象趋近。
这本书即偶用口语,沾染了一点“京味”
。
此书的读者,不难由征引文字,了解著者当年的阅读状况,以至1980年代的某种风气,即如引西书、用西典,食洋不化;无论“古希腊”
、“法国”
、“拉丁民族”
,还是“酒神”
、“日神”
,以至“欧洲中世纪”
、日本的“物之哀”
云云,无不一知半解。
薄弱的知识基础却无妨于写得兴会淋漓,以至我自己回头去读,会觉得饶舌,尤其想到那时1980年代已到了尽头。
这以后写作愈趋敛抑,习于删繁就简,才对当年的书写方式感到了陌生,对那一种工作状态,有了淡淡的怀念:看来写《城与人》时的我还不甚老。
北京师范大学版的《城与人》,选用了沈继光先生的近二十幅摄影作品。
结识沈先生,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作为媒介的,正是这本书。
沈先生那时在拍摄京城的胡同,后来又拍摄“老物件”
,拍摄乡野,成绩无不可观。
“城市改造”
早已将京城的胡同大片抹平。
再过一些日子,本书所描述的现象,不知还能否搜寻到相应的“实物”
作为见证?
赵园
2013年12月
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,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。
-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
- 签到十年,我成圣了逍遥火神
- 仙子的修行·美人篇yehou123
- 原来,她们才是主角(加料版)CCC
- 神豪的后宫日常大香蕉
- 人生如局笔龙胆
- 端庄美艳教师妈妈的沉沦无绿修改版佚名
- 在言情文里撩直男男主【快穿/np】辞奺
- 斗罗大陆之极限后宫(无绿改)3250027607
- 神女逍遥录Kom-凡
- 红颜政道饿狼咆哮
-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菇面要加蛋
- 绝世神器(御女十二式床谱)明日落花
- 女配她只想上床(快穿)黄心火龙果
- 戏里戏外(1v1)H苏玛丽
-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
- 掌中的美母幕卷
- 吾母美如画曹主任
- 乱伦豪门杨家假面阿飞
- 房客(糙汉H)无罪国度
- 交易沦陷在下小神j
- 众香国,家族后宫瘦不了
- 娱乐圈的不正常系统(修正版)霸王色
- 继女调教手册(H)奶油味香蕉
- 长安春华阙阙
- 绿意复仇——我的总裁美母安安大小姐
- 我和我的母亲(寄印传奇)气功大师
- 溺爱儿子的爆乳肥臀教师艳母,竟然是头痴女母猪(无绿修改版)琴师
- 蛊真人之邪淫魔尊千面兰
- 我在魔兽世界当禽兽晨世美
- 母上攻略竹影随行
- 无限之邪恶系统永恒的恒星
- 租赁系统:我被女神们哄抢!OVA
- 巨根正太和家族美熟女画纯爱的JIN
- 我的人渣指导系统(加料版)薛定谔的猫耳
- 斗罗大陆之极限后宫(无绿改)3250027607
- 斗罗大陆2蚕淫小六六
- 我的美母教师纳兰公瑾狼太郎
- 父债子偿拉大车的小马
- 我的冷傲岳母和知性美母因为我的一泡精液成为了熟女便器 (无绿版)hanshengjiang
- 娱乐圈的曹贼大龙很帅
- 原来,她们才是主角(加料版)CCC
- 美母如烟,全球首富佚名
- 宗主母亲与巨根儿子的淫乱性事stqyyy
-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
- 神豪的后宫日常大香蕉
- 美母的信念大太零
- 娱乐圈的不正常系统(修正版)霸王色
- 堕落的冷艳剑仙娘亲(大夏芳华)红炉点雪
-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
- 复仇恶女甜又飒,偏执病娇缠上瘾晨曦
- 六十岁离婚,系统才来王沐川
- 我在怪谈世界走钢丝[无限]卿本疏狂
- 高冷青梅,但暗恋我多年小橘子灯
- 为啥不信我是重生者叨狼
- 啊,今天陛下也很宠呢阿嗙
- 爱上学长当然是学长的错莫里_
- 九域凡仙道不易
- 催眠神瞳世间
- 人族镇守使白驹易逝
- 给你,我青涩的苹果Li季
- 袜香日记鱼神
- 穿成郡主和长公主he了沈俢竹
- 即将新婚的妻子却被他人调教青丝如墨
- 战神将军与笼中雀江夏JC
- 顶级Alpha她养了只冤种小鬼晚苍
- 帝国王权地噬洋葱
- 你们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好想看评论我什么都会做的
- 嫌弃我修为尽失,我成大帝你哭啥飞鸟与鱼
- 乌龙山修行笔记八宝饭
- 从现代归来的朱元璋墨守白
- 娘子,你不会真的给我下药了吧桃公旺
- 最强御女系统我不是水冰晶
- 救命!女装网骗被抓到怎么办梗翠花
- 鱼怎么能认猫当老婆?!甜掉牙
- 做大哥的男人几树
- 秘密情人幼望
- 说好对女O无感,他怎么咬我腺体小仙咕咕
- 纪录片创作教程韩永青
- 一胎三宝!战神要复合就是想屁吃女王在线浪
- 交响乐欣赏十八讲刘雪枫
- 黎糖糖的快穿之旅乐乐鱼啊
- 及时行乐:音乐生态综观解读林采韵
- 闷骚学霸开了窍,学渣软腰要折断吾无二
- 重生,回到小姨抱私生子回家前夜卿回
- 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:理论与方法涂冬波等著
- 狗狗A他攻了顶A指挥官豆腐军团
- 末世位面经营指南灿喵
- 王妃是妖界老祖宗,得宠着!冷清木
- 杀穿副本后,我在规则里养大邪神白桃呜呜龙